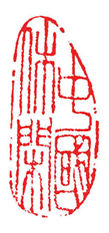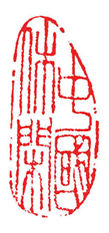【編發(fā)按】
本文是任大援先生為紀(jì)念“歐洲來華傳教士南懷仁誕辰400周年”而作,發(fā)表于《國際漢學(xué)》2023年第六期��。任大援是原中國藝術(shù)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���,深耕中�����、外文化思想史�����。1998年跟隨劉夢溪先生創(chuàng)辦《世界漢學(xué)》�����,秉持“為了中國��,為了過去與未來���,為了東方與西方”治學(xué)精神���,獨辟學(xué)術(shù)洞見與國際視野,在東����、西文明對話中筑起思想的界碑。帶著這份執(zhí)著扛鼎后起之秀《國際漢學(xué)》��。先后近四十春秋��,任先生闡釋傳教士群體在“西學(xué)東漸”與“中學(xué)西傳”中的雙向作用力��,表達了“究天人之際�,通古今之變”的學(xué)術(shù)境界。本文基于比利時人南懷仁傳教中國為起點�����,以史料考辨之功���、哲人睿智之力�����,將漢學(xué)研究從單一的文本考據(jù)升華為跨學(xué)科的文化互鑒����。全文雖僅三千余字,然論證縝密�����,思想深邃����,歷史線索清晰�,內(nèi)史外史兼顧,展現(xiàn)了深厚的學(xué)術(shù)造詣����。特薦之!(馬惠娣)
400年的回響
2023年是歐洲來華傳教士南懷仁(Ferdinand Verbiest 1623-1688)誕辰400周年����,同時也是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(Giulios Aleni, 1582—1649)的中文著作《職方外紀(jì)》(世界地理)在中國出版問世400周年。這些歷史事件�,在今天仍然值得關(guān)注。
歐洲的耶穌會士來華���,從羅明堅����、利瑪竇算起,已經(jīng)超過440年�����。由于傳教士的特殊身份����,過往的研究常常以“傳教史”視之,甚至不屑一顧���。孰不知這些人正是大航海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主力���,不容忽視。季羨林先生說���,“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發(fā)展�,促進人類科技文化增長���,加強人民與人民間�����、政府與政府間相互理解����,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?�!?sup>1 從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審視歷史��,近些年不斷有新的斬獲����,對這段歷史仍然有較大的研究探索空間�。
傳教士來華后,中西文明產(chǎn)生了哪些互鑒和促進呢���?
首先�,是傳教士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塊廣袤的大陸及其文明���,使歐洲人對中國悠久的歷史�、遼闊的疆域��、教育程度充分的百姓,以及政治與儒家道德的結(jié)合都表現(xiàn)出了欽佩之情��。波蘭傳教士卜彌格(Michel Boym �,1612-1659)繪畫的《中國地圖集》《中國植物志》對歐洲學(xué)者起到了振聾發(fā)聵的作用,使他們產(chǎn)生了學(xué)習(xí)和研究的渴望����,美國漢學(xué)家孟德衛(wèi)(David E. Mungello,說過��,“這樣的態(tài)度反映在當(dāng)時文獻中到處可見的一個詞中——這個詞就是curious (編者按:好奇的�、不尋常的)” 但他又接著指出,“這個詞在當(dāng)時的意思更接近于拉丁語中的形容詞curiosus�,指通過苛細(xì)的準(zhǔn)確性、對細(xì)節(jié)的注重和有技巧的調(diào)查才能得到的“不同尋?!钡氖挛铩���!?sup>2 他的這個解釋�����,明確地點出了傳教士學(xué)習(xí)中國文化時態(tài)度的認(rèn)真和實踐的深入�。利瑪竇早年用中文撰寫的一部重要著作是《交友論》����,他的寫作���,至少有兩個動機:一是說明西方也有重視交友的傳統(tǒng),借以拉近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距離�����;二是表明他與中國儒生志趣相投�,借以拉近傳教士與儒生的距離。 在這兩個動機的背后���,也顯示了對中國倫理的重視,這不僅是中國文化對其影響的結(jié)果���,也是他調(diào)適路線的一個思想基礎(chǔ)���。
在19世紀(jì)之前,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學(xué)習(xí)探索的最重要表現(xiàn)��,是對中國經(jīng)典的翻譯和編撰漢語與當(dāng)時各種歐洲語言(如拉丁語��、法語�、葡萄牙語����、西班牙語)的字典���。對這兩方面的研究��,近年來都有新的進展�。
在文明互鑒另一個側(cè)面���,是傳教士帶來的西學(xué)知識與方法推動了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演變�����。傳教士帶來的西學(xué)在晚明稱“天學(xué)”��,其義有二:一是“天算之學(xué)”����,二是“事天(主)之學(xué)”���。天算之學(xué)使儒生眼界大開���,找到了中國傳統(tǒng)格物窮理之學(xué)的新方向�����。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的《幾何原本》�,是西學(xué)進入中國后起核心作用的代表文獻�����。因為算學(xué)不僅是一切自然科學(xué)的基礎(chǔ)��,也是邏輯學(xué)與哲學(xué)的基礎(chǔ)���。傳教士帶來的西學(xué)到達中國之前����,儒學(xué)發(fā)展到宋明理學(xué)階段��,“格物致知”成為核心命題�,朱熹將格物致知解釋為“即物窮理”���,提出“即凡天下之物��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“����,3 但朱熹及其后學(xué)將”物“解釋為”事“,把格物的范圍集中在道德和政治的方面����,并不去探索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之理,至多也是清初學(xué)者把范圍擴充至文獻考據(jù)�,雖然說其中也具有歸納與演繹的科學(xué)精神,但范圍有限�。胡適做過這樣的比較:當(dāng)顧炎武寫出著名的音韻學(xué)著作《音學(xué)五書》(1680)的時代,西方的牛頓已經(jīng)發(fā)表了《自然哲學(xué)原理》(1687)�����,這一時代中國在科學(xué)上落伍了��。
《幾何原本》中文版(1607)的出現(xiàn)��,以及在此前后天文學(xué)�、地理學(xué)、邏輯學(xué)��、水利學(xué)等等的知識引入中國��,使得中國的“格致之學(xué)”和西方科學(xué)嫁接����,雖然開始時是少數(shù)人�����,但卻開拓出新的求知方向��。撰寫《職方外紀(jì)》的艾儒略在福建期間���,與之結(jié)交的中國文人有70多人。最近有年輕學(xué)者通過對方以智(1611-1671)《膝寓信筆》的研究���,挖掘與之交往的士人之西學(xué)背景���,探尋方以智與西學(xué)士人的西學(xué)知識交流,反映了當(dāng)時文人學(xué)者的一種風(fēng)氣����。他們后來在不同程度上,將西學(xué)的影響運用到學(xué)術(shù)研究中��,促進了中國學(xué)術(shù)的進步���。
以上只是概述式地指出了17世紀(jì)中西互鑒的案例����,在這種互鑒中�����,也有歷史的經(jīng)驗教訓(xùn)�。這種教訓(xùn),反映在西方����,是羅馬教廷的獨斷,案例是禮儀之爭����。在禮儀之爭中,羅馬教廷雖然反復(fù)多變�,但最終以狹隘的宗教立場處理與異文化的交流互動,禁止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調(diào)適路線��,最終造成傳教在中國被禁止的結(jié)局�,西學(xué)東漸也嚴(yán)重受阻。如果和中國的康熙皇帝做一個比較�����,后者采用實用主義的態(tài)度,賜予天主教堂“敬天”的匾額�����,與傳教士來往�,取得了己之所需,使西學(xué)為己所用����。
在中國的士大夫方面,甚至也包括康熙��,并沒有像傳教士那樣��,用拉丁語中的形容詞curiosus (好奇的�、悉心探究的)那樣的態(tài)度去看待西學(xué),一些人仍固守著儒學(xué)歷史悠久�、他人莫之能比的優(yōu)越心態(tài)。例如積極推動《西儒耳目資》(相當(dāng)于明代的漢語拼音)出版發(fā)行的晚明官宦學(xué)者王徵(1592-1666)�,他一方面寫了《三韻兌考》《西儒耳目資釋疑》的文章,對金尼閣(Nicolas Trigault�,1577-1628)的原著加以補充,一方面又說����,“蓋二十五字母,即太極中分之奇偶���,而兩字相比成音�����,即奇偶相重而為象也”4 云云���,說漢字注音的理論來源于周易的陰陽八卦之說,這幾乎和魏晉以來的“老子化胡說”如出一轍��。明末以來這樣的例子不少:一方面利用“西學(xué)”方法編寫出漢字的拉丁字母拼寫系統(tǒng)�、促進了漢字拼寫注音的進步,同時又認(rèn)為這種方法是來自中國古老傳統(tǒng)��,不足為奇��。這說明��,晚明實學(xué)思潮的流行雖然是一種歷史進步��,但當(dāng)中國儒生面對西學(xué)的沖擊��,誤將過時古董當(dāng)作不變的傳統(tǒng),未能更積極地對西學(xué)加以借鑒����,其結(jié)果是影響了中國科學(xué)的進步。
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最長于理論思維的學(xué)者�����,是當(dāng)時儒生的另一種類型�����。他著有《通雅》與《物理小識》��。其內(nèi)容“函雅故���,通古今”�,包括天文學(xué)���、物理學(xué)����、醫(yī)藥學(xué)��、生活科學(xué)等當(dāng)時的自然科學(xué)知識,因此被后人譽為中國明末清初“百科全書”式的學(xué)者�����。在他的著作中���,提出一個重要觀點,即“泰西質(zhì)測頗精���,通幾未舉�����?�!?sup>5 意思是西學(xué)中的科學(xué)縝密���,而哲學(xué)未逮。由于十七世紀(jì)西方的科學(xué)與哲學(xué)尚未分開�,哲學(xué)還被神學(xué)所統(tǒng)領(lǐng),在這個意義上�����,方以智的觀點是合理的,但是�,方氏對質(zhì)測之學(xué)的學(xué)習(xí)和把握,是否使用了如curiosus 那樣的鉆研態(tài)度呢��?這仍然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���。有過翻譯《幾何原本》經(jīng)歷的徐光啟在崇禎年曾就歷法研究上疏皇帝說:“欲求超勝��,必先會通����。會通之前����,必先翻譯?���!边@樣的觀點,并未成為當(dāng)時具有實學(xué)精神的多數(shù)知識分子的實踐��。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����。
傳教士來華400多年后的今天���,遺跡仍在,當(dāng)時中外學(xué)者交流互鑒的著作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整理�����,其產(chǎn)生的回響��,猶然不絕于耳���。就漢學(xué)研究者而言,當(dāng)有所思����。
(任大援)
1、季羨林:《“西學(xué)東傳人物叢書”總序》�����,見《勤敏之士——南懷仁》��,北京��,科學(xué)出版社����,2000年�,第1頁��。
2�����、《奇異的國度:耶穌會適應(yīng)政策及漢學(xué)的起源》��,鄭州�,大象出版社,2010年4月�����,“導(dǎo)言”��,第1-2頁��。
3�、《大學(xué)補傳》,《朱子全書》第6冊��,第20頁�。合肥���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10年9月�。
4、《西儒耳目資· 王徵序》�,北京,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本�����,1957年2月���。
5、方以智《通雅》���,北京�,中國書店���,1990年���,第37頁。
|